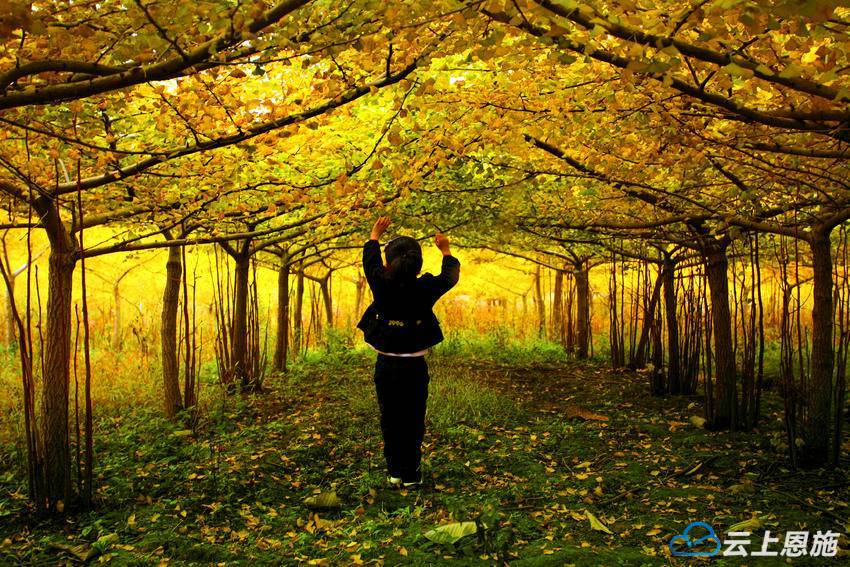云上恩施报道(利川通联记者 杜苗 通讯员 陈小林)鄂西利川的竹海,总在晨雾里透着股韧劲。当春风把楠竹的笋尖催得冒出土层时,竹农们便背着竹篓钻进林子——他们要找的不是成竹,而是刚抽枝的楠竹幼株,去孕育那坛藏在竹骨里的酒。这门诞生于民间、2019年跻身市级第五批非遗名录的竹筒酒技艺,酿的从不是简单的白酒,而是一场自然与时光的共生。



选竹是门看“骨相”的学问。老竹农蹲在竹林里,手指顺着幼竹的秆子轻轻摩挲,要选那些粗细如碗口、竹节间距均匀的苗子。“太细的竹腔装不下酒魂,太粗的竹腔散了竹香。”他们总这么说。选定的幼竹要做上记号,不是用墨,而是用竹刀在竹节处轻轻刻道浅痕——像是给自然递去一张约定的字条,等着日后赴一场酒的约会。




灌酒的时刻最见巧思。窖藏多年的纯粮白酒早已褪去了新酒的烈气,在陶坛里温得绵柔。竹农们捧着特制的高压灌注器,在幼竹的竹节侧面钻个细如麦芒的小孔——这“微创”的讲究,是怕伤了竹的脉络,就像给孩子打针要轻手轻脚。酒液顺着针头缓缓注入竹腔,听不到声响,却能看见竹秆微微泛出润泽的光,仿佛竹在悄悄吞咽这人间的醇酿。灌完后用竹蜡封住小孔,幼竹便带着这坛“腹中酒”,重新融进竹海的风里。


接下来的十个月,是最考验耐心的等待,也是竹筒酒最神奇的蜕变。酒在竹腔里不是静止的,它像个在竹身里游学的学子,一边慢慢释放甲醇、杂醇这些“戾气”,一边贪婪地吸收竹的养分——竹沥的清润、竹多糖的甘甜、竹叶黄酮的醇厚,都顺着竹的脉络,一点点渗进酒里。竹在长,酒也在长:竹秆拔高时,酒在竹腔里轻轻晃动,像是跟着竹的节奏呼吸;竹叶沙沙作响时,酒里便多了几分风的清冽。竹农们每月都会来竹林看一次,不用靠近,只看竹秆的颜色——若是泛着深绿的油光,就知道酒在里面长得好。


等到秋霜染黄了竹叶,便是取酒的日子。竹农们扛着砍刀来到竹林,对着做过记号的竹秆轻轻一砍——“咔嚓”一声,断面处立刻渗出晶莹的酒珠,顺着竹节往下滴,落在陶碗里发出“叮咚”的轻响。剥开竹壳,竹腔里的酒泛着淡淡的琥珀色,凑近一闻,没有纯白酒的冲劲,反而满是竹海的清香,像是把整座山林的灵气都装进了竹筒。

把装酒的竹筒扛回家,用心存放。用时,倒一杯在粗瓷碗里,酒液还带着竹的微凉。抿一口,先是竹的清甜在舌尖散开,接着是粮食酒的醇厚慢慢漫上来,最后余味里还留着点阳光的暖意——这口酒里,藏着竹的坚韧,也藏着时光的温柔。老辈人说,竹筒酒最懂“取舍”:酒舍了戾气,才得了竹的清雅;竹舍了部分养分,才成就了酒的独特。这不正是做人的道理?懂得放下多余的执念,才能在与自然的相处里,酿出属于自己的醇厚。
如今,这门技艺被好好地传承着。每当有人走进利川的竹海,总能看见竹农们在林间穿梭的身影——他们不是在砍竹,而是在守护一场场“竹与酒”的约定。这坛藏在竹骨里的酒,不仅留住了利川的味道,更留住了一份“慢下来”的智慧:好的东西,从来都需要时间的孕育,需要与自然的共生。
(来源:云上恩施 利川通联记者 杜苗 通讯员 陈小林 一审:和秋阳 二审:黄頔芳 三审:孙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