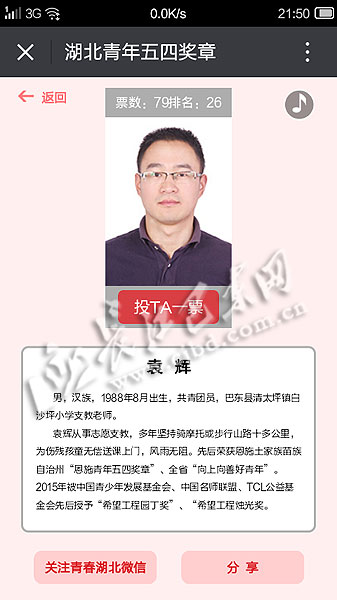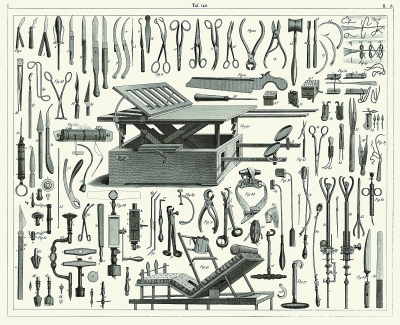
иҝ‘ж—ҘпјҢеұұеҜЁзүҲгҖҠдәәзұ»з®ҖеҸІгҖӢиў«жӣқе…үгҖӮиҜҘд№ҰеңЁж ҮйўҳгҖҒе°Ғйқўи®ҫи®ЎзӯүеқҮй«ҳд»ҝдәҶе°Өз“Ұе°”В·иө«жӢүеҲ©зҡ„гҖҠдәәзұ»з®ҖеҸІгҖӢпјҢдҪңиҖ…жҳҜдёҖеҗҚдёӯеӣҪиҒҢдёҡеҶҷжүӢпјҢз«ҹеҸ–дәҶдёҖдёӘдәҡзү№дјҚеҫ·зҡ„вҖң笔еҗҚвҖқгҖӮиҜҘд№Ұеӣ иҙЁйҮҸдҪҺеҠЈпјҢиў«зҪ‘еҸӢй…·иҜ„дёәпјҡвҖ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һҒз«ҜдёҡдҪҷзҡ„еҺҶеҸІиҜ»иҖ…пјҢж•ҙжң¬д№Ұ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з»ҷжҲ‘д»»дҪ•жңүи§Ғең°зҡ„ж–°еҶ…е®№е’ҢзҹҘиҜҶзӮ№вҖҰвҖҰе–ӮзӢ—йғҪдёҚж„ҝж„Ҹз»ҷиҝҷдёӘгҖӮвҖқ
з®ҖеҸІйҒӯеұұеҜЁпјҢжҸӯеҮәвҖңз®ҖеҸІзғӯвҖқиғҢеҗҺзҡ„е°ҙе°¬гҖӮ
вҖңз®ҖеҸІзғӯвҖқжҳҜиҝ‘е№ҙжқҘеӣҫд№ҰеёӮеңәзҡ„дёҖиӮЎжҡ—жҪ®пјҢеңЁеҗ„еӨ§зҪ‘еә—пјҢжҗңзҙўвҖңз®ҖеҸІвҖқдәҢеӯ—пјҢз«ӢеҲ»дҫҝжңүиҝ‘еҚғз§Қеӣҫд№Ұж¶ҢжқҘпјҢд»ҺгҖҠдәәзұ»з®Җ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дё–з•Ңз®ҖеҸІгҖӢеҲ°гҖҠдёҮзү©з®Җ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е®Үе®ҷз®ҖеҸІгҖӢпјҢз”ҡиҮіиҝҳжңүгҖҠй»‘жҙһз®ҖеҸІгҖӢгҖӮ
е…¶е®һпјҢгҖҠй»‘жҙһз®ҖеҸІгҖӢиӢұж–ҮеҺҹеҗҚдёәгҖҠй»‘жҙһгҖӢпјҢиҖҢгҖҠйҮ‘иһҚеҚұжңәз®ҖеҸІпјҡ2000е№ҙжқҘзҡ„жҠ•жңәгҖҒзӢӮзғӯдёҺеҙ©жәғгҖӢиӢұж–ҮеҺҹеҗҚдёәгҖҠйҮ‘й’ұиәҒзӢӮз—Үпјҡд»ҺеҸӨзҪ—马еҲ°еӨ§еҙ©жәғзҡ„з№ҒиҚЈпјҢжҒҗж…Ңе’ҢжіЎжІ«гҖӢгҖӮиҖҢиӢұж–ҮеҺҹеҗҚгҖҠжҲ‘们зҡ„еӨӘйҳігҖӢпјҢиҮӘ然дјҡиў«иҜ‘жҲҗгҖҠеӨӘйҳіз®ҖеҸІгҖӢгҖӮ
жҳҫ然пјҢеӨ§е®¶йғҪеңЁжҗӯз®ҖеҸІзҡ„дҫҝиҪҰгҖӮиҜ»иҖ…еҜ№з®ҖеҸІдҪ“дҫӢдёҚз”ҡзҶҹжӮүпјҢд№ҹз»ҷй’»з©әеӯҗиҖ…йў„з•ҷдёӢз©әй—ҙгҖӮ
з®ҖеҸІз©¶з«ҹжҳҜ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
зҺ°д»Јз®ҖеҸІеҶҷдҪңдј з»ҹжәҗиҮӘиҘҝж–№пјҢиҲ¶е…ҘдёӯеӣҪдёҚиҝҮзҷҫдҪҷе№ҙгҖӮ
зҺ°д»Јз®ҖеҸІжӨҚж №дәҺиҘҝж–№дәәеҜ№еҺҶеҸІ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еҚіпјҡеҺҶеҸІе№¶йқһжӣҫз»Ҹ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Ӣ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дёӘд»ҺдҪҺеҗ‘й«ҳгҖҒд»Һз®ҖеҚ•еҲ°еӨҚжқӮзҡ„еҸ‘еұ•иҝҮзЁӢгҖӮжІЎжңүеҸ‘еұ•пјҢе°ұжІЎжңүеҺҶеҸІгҖӮжӯЈеҰӮж— дәәе…іеҝғиӢҚиқҮдё–з•ҢиҝҮеҺ»еҮ зҷҫе№ҙеҸ‘з”ҹдәҶе“ӘдәӣйҮҚеӨ§дәӢ件пјҢеӣ иӢҚиқҮжңӘеҸ‘з”ҹиҝӣеҢ–пјҢжүҖд»Ҙе®ғжІЎжңүеҺҶеҸІгҖӮ
й»‘ж је°”жӣҫиҜҙпјҡвҖң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»Һжң¬иҙЁдёҠзңӢжҳҜжІЎжңүеҺҶеҸІзҡ„пјҢе®ғеҸӘжҳҜеҗӣдё»иҰҶзҒӯзҡ„дёҖеҶҚйҮҚеӨҚиҖҢе·ІпјҢд»»дҪ•иҝӣжӯҘйғҪдёҚеҸҜиғҪд»Һдёӯдә§з”ҹвҖҰвҖҰ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дёӯеӣҪд»»дҪ•дёҖж¬Ўйқ©е‘ҪйғҪжІЎиғҪдҪҝиҝҷдёӘеҺҶеҸІж”№еҸҳгҖӮвҖқиҝҷеҪ“然жҳҜеҒҸи§ҒпјҢеҚҙдҪ“зҺ°дәҶиҘҝж–№дәәзҡ„еҺҶеҸІи§ӮгҖӮ
дәҺжҳҜпјҢеҺҶеҸІеӯҰиҖ…зҡ„д»»еҠЎе°ұжҲҗдәҶж №жҚ®еҸІж–ҷеҺ»еҜ»жүҫеҸ‘еұ•зәҝзҙўпјҢиҖҢз”ЁжҰӮжӢ¬зҡ„笔法еҶҷеҮәиҮӘе·ұзҡ„еҸ‘зҺ°пјҢеҚідёәз®ҖеҸІгҖӮ
з®ҖеҸІеңЁдёӯеӣҪеҸ—еҲ°ж¬ўиҝҺ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®ғдёҺдёӯеӣҪеҸӨдәәзҡ„йҖҡеҸІеҶҷдҪңдј з»ҹжңүжҡ—еҗҲеӨ„пј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ЁдәЎеӣҪзҒӯз§Қзҡ„еҺӢеҠӣдёӢпјҢз®ҖеҸІдҫҝдәҺжҺЁе№ҝпјҢеҸҜд»Ҙе”ӨйҶ’е…ұеҗҢзҡ„иә«д»Ҫж„ҸиҜҶгҖӮ
жҲ‘еӣҪж—©жңҹз®ҖеҸІеӨҡдёәж•ҷжқҗпјҢ并йҖҡиҝҮиҜҫе Ӯж•ҷиӮІж·ұе…ҘеҲ°дәә们зҡ„ж„ҸиҜҶдёӯпјҢз”ҡиҮіеҜ№и®ёеӨҡдәәзҡ„и§ҶйҮҺгҖҒжҖқжғіж–№жі•дә§з”ҹдәҶеҶіе®ҡжҖ§еҪұе“ҚгҖӮеҚідҪҝе‘ҠеҲ«дәҶиҜҫе ӮпјҢ他们д»ҚдёҖз”ҹжҠҠз®ҖеҸІйҳ…иҜ»и§ҶдёәвҖңй•ҝзҹҘиҜҶвҖқвҖңеҸ—ж•ҷиӮІвҖқгҖӮиҝҷеӣә然еҲӣйҖ еҮәдёҖдёӘе·ЁеӨ§зҡ„з®ҖеҸІйҳ…иҜ»зҫӨпјҢдҪҶд№ҹжүӯжӣІдәҶз®ҖеҸІзҡ„жң¬ж„ҸгҖӮ
з®ҖеҸІжң¬жҳҜвҖңз”ұеҸІе…Ҙе“ІвҖқпјҢеҰҷеңЁеҸ‘зҺ°гҖҒеҪ’зәідёҺиҜҒжҳҺ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з»“жһң并дёҚйҮҚиҰҒгҖӮеҸҜеңЁдёӯеӣҪиҜ»иҖ…зңӢжқҘпјҢз®ҖеҸІе°ұжҳҜвҖңе“ІзҗҶ+зҹҘиҜҶзӮ№вҖқпјҢйғҪжҳҜзЎ®е®ҡж— з–‘зҡ„дёңиҘҝгҖӮ
з®ҖеҸІжң¬иә«жңүдёӨеӨ§з—…
еҜ№з®ҖеҸІжҠұжңүиҝҮй«ҳжңҹжңӣпјҢжҳ“еҝҪз•Ҙе…¶дёӯйЈҺйҷ©пјҢеҚіз®ҖеҸІеҫҲеҸҜиғҪж»‘еҗ‘вҖңиҫүж јеҸІеӯҰвҖқгҖӮ
жүҖи°“вҖңиҫүж јеҸІеӯҰвҖқпјҢеҚівҖңеҺҶеҸІзҡ„иҫүж ји§ЈйҮҠвҖқгҖӮиҫүж је…ҡжҳҜ19дё–зәӘеҲқиӢұеӣҪзҡ„дёҖдёӘж”ҝжІ»з»„з»ҮпјҢе…¶дёӯеӯҰиҖ…еёёд»ҺеҺҶеҸІдёӯжүҫж №жҚ®пјҢд»ҘдёәиҮӘе·ұзҡ„ж”ҝи§Ғиҫ©жҠӨгҖӮ
вҖңиҫүж јеҸІеӯҰвҖқжңүдёӨеӨ§зү№иүІпјҡйҰ–е…ҲпјҢе°ҶзҺ°жңүзҡ„дёҖеҲҮи§ҶдёәжңҖжӯЈзЎ®зҡ„пјҢжҳҜвҖңеҺҶеҸІеҝ…然вҖқзҡ„дә§зү©пјӣе…¶ж¬ЎпјҢжҲӘеҸ–жқҗж–ҷпјҢзј–йҖ еҺҶеҸІеҸ‘еұ•и§„еҫӢпјҢд»ҘжӯӨжҺЁж–ӯжңӘжқҘвҖңеҝ…然вҖқдјҡеҰӮдҪ•гҖӮ
д»ҺеүҚиҖ…жқҘиҜҙпјҢеҫҲе®№жҳ“иҗҪе…ҘдёәзҺ°еӯҳдәӢзү©жүҫеҖҹеҸЈзҡ„йҷ·йҳұпјҢжҢүиҝҷдёӘйҖ»иҫ‘пјҢзј и¶ід№ҹжңүвҖңеҝ…然жҖ§вҖқ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ҳиҰҒж”№еҸҳе‘ўпјҹд»Һз»“жһңйҖҶжҺЁеҺҹеӣ пјҢеҝ…然иө°иҝӣжӯ»иғЎеҗҢгҖӮ
д»ҺеҗҺиҖ…жқҘиҜҙпјҢеҲҷжҳҜе°Ҷзү©зҗҶдё–з•Ңзҡ„规еҫӢзЎ¬еҘ—еҲ°дәәж–Үдё–з•ҢдёӯгҖӮеңЁзү©зҗҶдё–з•ҢдёӯпјҢ规еҫӢеӯҳжңүеҜ№з§°жҖ§пјҢдёҚеӣ ж—¶з©әж”№еҸҳиҖҢж”№еҸҳпјҢеҸҜд»Ҙж №жҚ®иҝҮеҺ»жқҘйў„жөӢжңӘжқҘгҖӮдәәж–Үдё–з•ҢеҲҷдёҚеҗҢпјҢеҸӨд»Јжңүж•Ҳзҡ„ж–№жі•еңЁд»ҠеӨ©еҸҜиғҪж— ж•Ҳ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еӣҪ家жңүж•Ҳзҡ„ж–№жі•еңЁйӮЈдёӘеӣҪ家еҸҜиғҪж— ж•ҲгҖӮйҡҸзқҖзҺҜеўғгҖҒж—¶й—ҙгҖҒжқЎд»¶зҡ„ж”№еҸҳпјҢ规еҫӢжң¬иә«д№ҹдјҡж”№еҸҳ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зңҹиғҪж №жҚ®иҝҮеҺ»зҡ„жүҖ谓规еҫӢжқҘйў„жөӢжңӘжқҘеҗ—пјҹ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жҷ®йҖӮжҖ§гҖҒеҸҜйҖҡзәҰжҖ§е’ҢеҜ№з§°жҖ§пјҢеҸҲжҖҺд№ҲиҜҒжҳҺиҝҷдәӣ规еҫӢдёҚжҳҜе№»и§үе‘ўпјҹ
йҒ—жҶҫзҡ„жҳҜпјҢеҺҶеҸІжқҗж–ҷж— йҷҗдё°еҜҢпјҢдёҚи®әжҢҒдҪ•з§Қи§ӮзӮ№пјҢйғҪдёҚйҡҫжүҫеҲ°зӣёеә”еҸІе®һпјҢ并梳зҗҶеҮәдёҖжқЎзәҝзҙўжқҘгҖӮеҺҶеҸІеҒҸи§ҒеёҰжңүиҮӘи¶іжҖ§пјҢе®ғдјҡиҮӘеҠЁеҜ»жүҫиҜҒжҚ®пјҢдҪҝдәәеңЁиҜҜдјҡдёӯи¶Ҡйҷ·и¶Ҡж·ұгҖӮ
дёәеҗҲйҖ»иҫ‘дёҚжғңзј–йҖ
еҚід»Ҙиў«еұұеҜЁзҡ„гҖҠдәәзұ»з®ҖеҸІгҖӢи®әпјҢд№ҹдёҚеӨӘз»Ҹеҫ—иө·жҺЁж•ІпјҢд№ҰдёӯејҘжј«зқҖвҖңиҫүж јеҸІеӯҰвҖқзҡ„е‘ійҒ“гҖӮжҜ”еҰӮдҪңиҖ…и®ӨдёәвҖңеҸІдёҠжңҖеӨ§зҡ„йӘ—еұҖвҖқжҳҜдәәзұ»еӯҰдјҡиҖ•з§ҚпјҢжІҰдёәеңҹең°зҡ„еҘҙйҡ¶пјҢз»қеӨ§еӨҡж•°еҶңж°‘з”ҹжҙ»дёҚжҜ”зҢҺдәәжӣҙе№ёзҰҸгҖӮеҸҜвҖңе№ёзҰҸвҖқжҳҜдёҖдёӘе®ўи§Ӯж ҮеҮҶе‘ўпјҹиҝҳжҳҜдёҖз§ҚжғіиұЎпјҹиҜҘд№ҰдёҚиҝҮжҳҜе°ҶеүҚд»ЈеӯҰиҖ…зҡ„зҺҜеўғеҶіе®ҡи®әгҖҒдҝЎжҒҜи®әзӯүжқӮзі…иө·жқҘпјҢж—ўе°‘еҲӣе»әпјҢеҸҲж— е®һиҜҒпјҢеҸӘжҳҜдҪңиҖ…е–„дәҺз«ҷеңЁйҒ“еҫ·еҲ¶й«ҳзӮ№дёҠпјҢж…·ж…ЁжҝҖжҳӮдёҖз•ӘпјҢдҝЁз„¶еҫҲвҖңиҮӘ然вҖқеҫҲж·ұеҲ»гҖӮеҰӮжӯӨдёҖжң¬зјәд№ҸиҗҘе…»зҡ„йҖҡдҝ—д№ӢдҪңпјҢиҜ‘жҲҗдёӯж–ҮеҗҺз«ҹиҺ·еҘ–ж— ж•°пјҢдҪ“зҺ°еҮәжҲ‘们зҡ„йҳ…иҜ»з•ҢеҜ№вҖңиҫүж јеҸІеӯҰвҖқжҳҜеӨҡд№Ҳзјәд№Ҹе…Қз–«еҠӣгҖӮ
з®ҖеҸІзҜҮе№…иҫғе°ҸпјҢеҫҖеҫҖеҸӘдҪҝз”ЁиғҪиҜҒжҳҺдҪңиҖ…и§ӮзӮ№зҡ„еҸІж–ҷпјҢжҠӣејғдёҺд№ӢзӣёеҸҚзҡ„еҸІж–ҷпјҢдҪҝжң¬жқҘдё°еҜҢзҡ„еҺҶеҸІеҸҳеҫ—з®ҖеҚ•гҖҒжё…жҷ°пјҢиҝҷз§Қжё…жҷ°еёҰжңүе·ЁеӨ§зҡ„иҜұжғ‘еҠӣпјҢиҜұдҪҝдәәиҮӘйҖ еҸІж–ҷпјҢд»ҘиЎҘйҖ»иҫ‘зјәзҺҜгҖӮ
еҰӮеҸІеӯҰеӨ§е®¶йәҰе…Ӣе°је°”еңЁгҖҠдё–з•ҢеҸІгҖӢдёӯдёәиҜҒжҳҺвҖң科жҠҖеҶіе®ҡеҺҶеҸІвҖқпјҢз«ҹиҷҡжӢҹеҮәдёҠеҸӨжңүжҲҳиҪҰе…өпјҢд»ҺдёӯдәҡдёҖзӣҙжү“еҲ°дёӯеӣҪпјҢиҝҷж”ҜиҖғеҸӨд»ҺжңӘеҸ‘зҺ°иҝҮзҡ„зҘһеҘҮд№ӢеёҲе°ҶдёңиҘҝж–№ж–ҮжҳҺиһҚдјҡиҙҜйҖҡпјҢдҪҝиҜёеӨҡз–‘жЎҲйғҪеҫ—еҲ°вҖңеҗҲзҗҶи§ЈйҮҠвҖқгҖӮ
еҶҚеҰӮй’ұз©Ҷе…Ҳз”ҹеңЁгҖҠдёӯеӣҪеҺҶд»Јж”ҝжІ»еҫ—еӨұгҖӢдёӯпјҢдёәиЎЁзӨәвҖңе…ҲеүҚйҳ”вҖқпјҢеұ…然е°Ҷе”җд»ЈдёүзңҒеҲ¶и§ҶдёәвҖңдёүжқғеҲҶз«ӢвҖқзҡ„йӣҸеҪўпјҢеҸҜ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дёүзңҒзҡҶжәҗиҮӘзҡҮ家зҡ„з§ҳд№Ұжңәжһ„гҖӮ
дёәдәҶжұӮйҖҡпјҢдёҚжғңз”ЁжғіиұЎжӣҝд»ЈеҺҶеҸІгҖӮеӨ§еӯҰиҖ…е°ҡдё”йҡҫе…ҚпјҢжҷ®йҖҡиҜ»иҖ…жӣҙжҳ“е…ҘеҪҖгҖӮ
иҜҘз”ЁжҖҺж ·зҡ„е§ҝеҠҝжү“ејҖз®ҖеҸІ
з®ҖеҸІеҸ—иҝҪжҚ§пјҢеҫҲеҸҜиғҪжҳҜзҺ°д»Јж•ҷиӮІдёӨдёӘжңҖеқҸжҲҗжһңзҡ„з»“еҗҲпјҡе…¶дёҖжҳҜз”ЁдәәйҖ йҖ»иҫ‘иҙҜз©ҝдёҖеҲҮпјҢдёҚиҝҪжұӮдҪ“йӘҢдёҺи¶Је‘іпјҢд»…ж»Ўи¶ідәҺвҖңиЎЁйқўзҡ„еҚҡеӯҰвҖқпјӣе…¶дәҢжҳҜзҹҘиҜҶиҮідёҠи®әпјҢе°ҶеӨҡи®°еҮ дёӘдәәзү©дёҺе№ҙд»ЈзңӢеҫ—жҜ”зӢ¬з«ӢжҖқиҖғгҖҒжҷәж…§зӯүжӣҙйҮҚиҰҒгҖӮ
иҜ»е®ҢгҖҠдёҮзү©з®ҖеҸІгҖӢпјҢе°ұиғҪд»ЈжӣҝжҲ‘们еҜ№дёҮзү©зҡ„ж„ҹеҸ—еҗ—пјҹиҜ»е®ҢгҖҠе®Үе®ҷз®ҖеҸІгҖӢпјҢе°ұж Үеҝ—зқҖдё–й—ҙеӨ§йҒ“зҡҶеӨҮжҲ‘жүӢдәҶеҗ—пјҹеҖјеҫ—жЈҖи®Ёзҡ„еҖ’жҳҜпјҡдёәд»Җд№ҲжҲ‘们дјҡдә§з”ҹиҝҷдәӣеҘҮжҖӘзҡ„жғіжі•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иҜ»ж•ҷ科д№ҰејҸзҡ„ж–Үжң¬пјҢиғҪдҪҝжҲ‘们дә§з”ҹеҝ«ж„ҹ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жҲ‘们дјҡеҰӮжӯӨиҪ»дҝЎз®ҖеҸІдёӯзҡ„дёңиҘҝпјҹ
еңЁж—Ҙжң¬пјҢз®ҖеҸІеӨҡз”ұеӨ§е®¶д№ҰеҶҷпјҢеӣ дёәвҖңз”ұеҸІе…Ҙе“ІвҖқеҫҲе®№жҳ“иў«иҜҜз”ЁдёәвҖңд»ҘеҸІиҜҒе“ІвҖқпјҢе…Ҳжңүи®әзӮ№пјҢеҶҚжүҫи®әжҚ®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вҖңжҲҸиҜҙвҖқе·ІжҲҗйЈҺе°ҡпјҢж— йқһвҖңйҮҺеҸІвҖқвҖңз§ҪеҸІвҖқгҖӮеҸӘжңүз»ҸиҝҮй•ҝжңҹдё“дёҡи®ӯз»ғзҡ„еӨ§еӯҰиҖ…пјҢж–№иғҪдёҚе •иҗҪиҮіжӯӨгҖӮ
еҗ•жҖқеӢүгҖҒй’ұз©ҶгҖҒйЎҫйўүеҲҡгҖҒиҢғж–ҮжҫңгҖҒзҝҰдјҜиөһзӯүе…Ҳз”ҹйғҪжӣҫеҶҷиҝҮз®ҖеҸІпјҢеҸҜйҒ—жҶҫзҡ„жҳҜпјҢеӣ 收е…ҘдёҚеӨҡпјҢдё”дёҚи®Ўе…ҘеӯҰжңҜжҲҗжһңпјҢдё“дёҡеӯҰиҖ…еҫҖеҫҖдёҚеҶҷз®ҖеҸІгҖӮж°ӣеӣҙеҰӮжӯӨпјҢеҰӮд»ҠзңӢз®ҖеҸІиҖҢиғҪдёҚеҸ—иҜҜеҜјпјҢе·Ійқһжҳ“дәӢпјҢеҲҷжңҖеҘҪзҡ„еҠһжі•жҳҜеӨҡзңӢеҮ з§ҚпјҢи§ӮзӮ№еҪјжӯӨдёҚеҗҢпјҢеҸҜзҹҘеҺҶеҸІжң¬жқҘеӨҡе…ғпјҢеә”иҜҘи¶ҠиҜ»и¶ҠеҺҡпјҢдёҚиғҪи¶ҠиҜ»и¶Ҡи–„гҖӮ
жқҘжәҗпјҡеҢ—дә¬жҷҡжҠҘ
пјҲиҙЈд»»зј–иҫ‘ йғңжңҲйЈһпјү